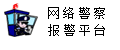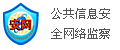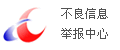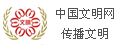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展过程中,借助强大的网络信息传播方式,民众对疫情的进展、政府的监管力度以及病毒防控的医学常识有了快速而便捷的获取路径,这与2003年的SARS疫情时期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高度的信息化和网络化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每天被裹挟在铺天盖地的信息洪流中,对信息的有用性、真实性、科学性的识别难度大大增加,而每个人又都有各自的知识边界和盲区,因此对收到信息源的理性分析,合理质疑的能力变得尤为重要。因为,比病毒传播更可怕的是恐慌的传染,如果我们缺乏科学的理性的“免疫力”!
最近在某微信公众平台上读到一篇微文,大致内容是因武汉某医院检验操作人员被感染,而推测是新冠病毒在血液标本产生气溶胶感染所致。虽只是个推测,虽然作者的意图可能是提醒操作人员注意风险防控,但是我底下的留言区里发现有些留言已经流露出明显恐慌的情绪,特别是很多恐慌还来自于年轻的基层检验人员。作为一名在检验科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检验人员,我想自己有责任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分享一下我对此信息的一些分析和探讨。
作为检验人员,无论是常态下的日常工作中还是在流行病的疫情期,我们在做患者样本检测时,其实是一直身处病原微生物的感染风险中。因此,如何正确自我防护,如何识别何种病原体、在何种标本中及何种操作中是有高感染风险变得尤为重要。这不仅需要检验人员具备更专业的病原微生物知识以及感染防控常识,更需要每位检验人员具有遇事不慌、理性分析,合理把控风险的能力。
通常我们认知的病原微生物的传播途径主要分为以下三种:接触传播、飞沫传播、空气传播(气溶胶传播)。
接触传播
“接触传播”相对比较容易理解,即病原体通过黏膜和皮肤的直接接触传播,所以我们检验人员在样本整个接触和检测过程中都需要戴手套。而“飞沫传播”和“气溶胶传播”可能大家对这两者的理解会有些混淆。
飞沫传播
“飞沫传播“一般是直径大于5um的含水颗粒,通过一定的距离(一般1米以内)进入易感的粘膜表面。由于飞沫颗粒较大、会很快沉降,不会长期悬浮在空气中。如果距离太近,飞沫会通过咳嗽、说话等行为掉落在对方的黏膜上产生感染,所以与被感染者保持一定的距离或佩戴防护口罩很有必要。目前新冠病毒的已经明确的主要传播途径是“飞沫传播”。
空气传播
而“空气传播”,即我们检验人员常提及的“气溶胶传播“,一般认为是直径小于5um,能长时间远距离散播后仍有传染性的颗粒。检验科的日常工作中最容易产生气溶胶的是微生物涂片、培养、PCR等操作环节以及血液样本离心过程等。
此次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期间,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颁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4版)》中,传染途径中明确:经呼吸道飞沫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亦可通过接触传播。
所以,是否存在气溶胶传播途径需要基于严谨的流行病学分析研究,不能仅凭某个孤立的事件而随意判断,我们更要针对该事件做很多排他性的分析。
1
首先,是否已明确排除了这四名检验科人员没有其他任何的“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的可能性?
其次,这四名被感染的检验人员是否都属于某一个专业检验组(核酸检测组?免疫组?生化组?还是临检组?)还是在不同的专业组?这个信息的确认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是归属于同一专业组,那么即使是怀疑气溶胶感染,对于产生气溶胶的标本类型可以进一步锁定。
2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是,对于大量存在于呼吸道样本中的新冠病毒,如果在患者血液中存在,那患者一定是已经进入到及其严重的病毒血症状态。我没能查到目前临床上已确诊的患者中发展到病毒血症比例是多少。但是这个数据能帮助我们客观的分析血液标本出现新冠病毒气溶胶感染的可能性大小。
3
最后,还有一个假设,如果真的是血液样本气溶胶引起的感染,那么所有暴露在这个所谓被气溶胶污染的实验室环境里,所有和开盖血样本接触的生化、免疫、临检检验人员可能都存在极大的被感染风险,而目前我们知道的是这个检验科只有四名检验人员被感染了。
还是回到我最初的那个点,在信息的洪流中,我们要学会多问几个“是什么,为什么,如果……会怎么样”?只有这样,我们下次再面对类似的问题时才能在有理有据的分析基础上合理管控风险,既不会无知无畏,也不会因噎废食、裹足不前。
人,一个有思想的人,首先要拥有质疑的精神,才能引领我们去探索未知,去伪存真,才能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边界!我想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每一个人,特别在每一个领域有自己专长的人,都应该用负责任的态度、用专业的精神、用理性的思考去帮助身边的人消除无谓的恐慌,树立信心和信任的基石去面对不确定性。比病毒传播更可怕的,是不经思考的轻信和盲从,是轻信和盲从下的恐慌,尤其是在这信息化的大时代下!
最后,还是要提醒战斗在繁忙的医学检验岗位的同仁们,不管是疫情状态下还是常态化工作中,都要按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做好科学防护,正确穿戴帽子、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品。保护好自己的健康,才能守护住病人的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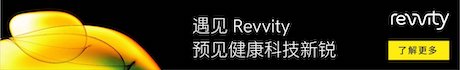



 /3
/3 





 浙公网安备33010802005999号
浙公网安备33010802005999号